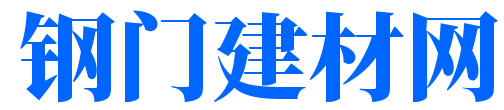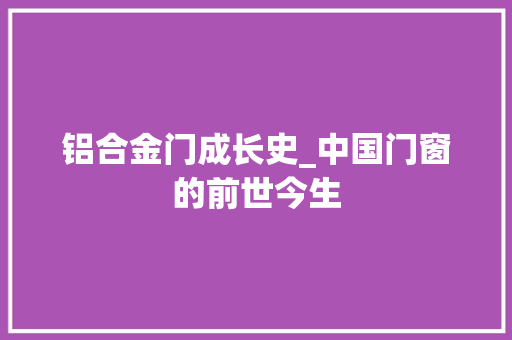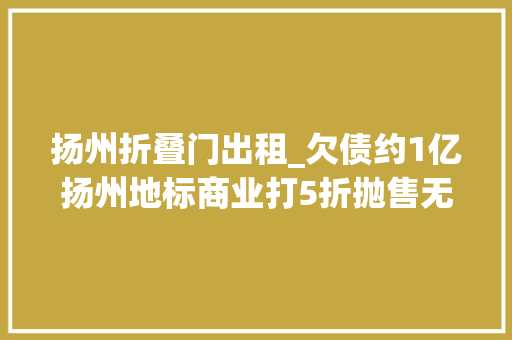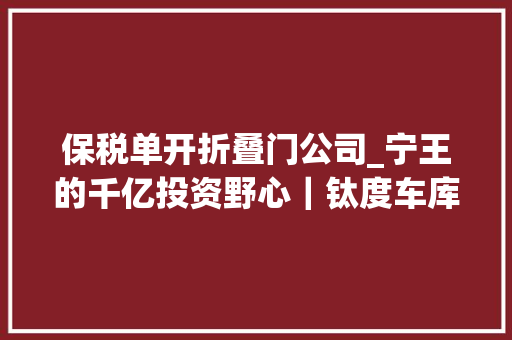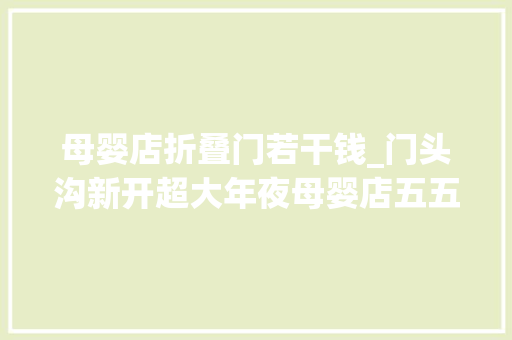这一过程,无疑是环球化经济消长以及文化博弈的隐喻。沉淀多年后,仍旧记得当初构建这一隐喻的载体——食品——国际连锁快餐与孤绝的饮食传统。无可否认,这一场景构成了我撰写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朱雀》的原由之一。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,被少女程囡引领入金陵古城,是在一个叫作“西市”的地方,那里有“秦淮八绝”。一碗鸭血粉丝汤,调动了游子的味蕾,也终于联结了与其原乡的文化根系。大约这便是学者张光直师长西席所说: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路子是通过它的胃。个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,亦包含对影象的唤醒。中国人对地缘的观点,是绕不开食品的。一方水土一方人,个中已包含食品对空间的定义。《北鸢》的卢家睦异地商贾,灾年施济发放家乡食品“炉面”,是德行,亦是不忘其本,本色是出于对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时刻不忘的情结。这个中所包含的,是食品对时空的穿透。而今,《燕食记》是一部以“食”为题的小说,其意便在这穿透: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,穿透岭南漫袤的近当代史;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进程,穿透地缘、民气世相的变迁。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章,有关食品的陈述漫长、绵延,与韶光干系。“溘然,往事浮现在我的面前。这味道,便是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。”感性而丰腴,是此后幽漫的影象大厦的阶梯。美食可以定格日常,亦定格历史。在作了大量案头与野外稽核之后,我将《燕食记》与一座茶楼的过往相联。这是岭南最为温暖的日常空间,有关这部小说的影象,一定带着南粤点心与氤氲的茶喷鼻香。喷鼻香港最古早的茶楼叫杏花楼,孙中山等人便是在这茶楼包间里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的,并确认叛逆成功后成立共和国政府。在这茶喷鼻香中,我意识到一些主要的时候被定义。饮食空间的流转与历史的推进所交汇,玉成日常与时期的同奏共跫,甚而被相互见证。核阅史传传统的渊源,久远如“鸿门宴”,区区三字,已包含食品、地点与韶光的交缠,更指向人性与政治的博弈。《燕食记》中向太史说:“当年我和兄长,同师从追随康南海,同年中举,同具名公车上书,但命运殊异。我和他吃的末了一餐饭,只一道菜,便是这菊花鲈鱼羹。只一壶酒,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。”个人影象与家国影象的纠缠,凝集于味觉,可说是一种化繁为简,也是一种可被当下复刻的文化密码。而这种密码也因其日常与平朴,便呈现出“大国”与“小鲜”之间的辩证。从“庙堂”至“民间”,一如小说之源,犹似田稗,不涉大雅,却生命力兴旺。以食品喻时期,也是由日常态度看历史兴颓,各类各样,万法归宗于民间。写《燕食记》,稽核时期,亦发掘民间。那是一个又一个砥实的瞬间,下面埋藏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内核。如新年时的黄沙大蚬,“大显”寄托岭南经世致用的代价不雅观;清明前后的产于乡间的“礼云子”,则以《论语》映照中国人的庄雅与体面。由于关乎节气,这些时候稍纵即逝。如学者李敬泽师长西席所言:“这盛大人间中,舌上之味、耳边之声,最易消散,最难留住,也最具根性,最堪安居。”其根性来自于对传统的衔接、世代的通报。由于共同的感性体验,以之为传统实现与理性的附丽,唤醒共通的民族基因,也构成了另一种穿越国族的想象的共同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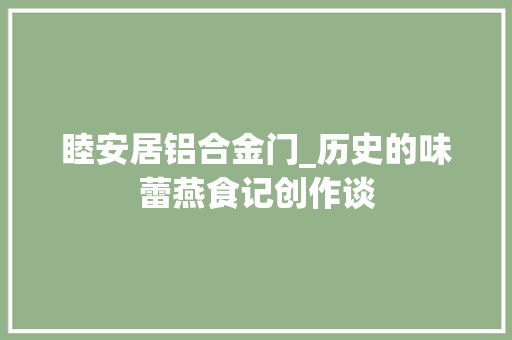
当然,在这漫长的通报中,势必要经历变革的磨练。中国人是不畏变革的,“变则通,通则久”。“变”与“常”,互为条件与目的。这一点,我曾借《北鸢》中昭如之口说出“中国人的那些道理,都在这吃里头了”。善待变,造诣了许多的美食。只一个豆腐,毛豆腐、臭豆腐、豆腐乳一源而至百变。由此,《北鸢》里写科举废除仕途无从后,知识分子的转型。设帐传授教化有之、掷笔从戎有之、投身商贾有之。而《燕食记》中的向太史出于钟鼎之家,于家国大义,作为逊清翰林看清了时期进步的走向,毅然支持民主革命,立起广州共和的大旗,而后又与子侄共襄抗日大计,是为勇。于个人奇迹,身离官场,担当烟草公司的总代理,开设当代化农场,是为识。“读书为重,次即农桑,取之有道,工贾何妨”,这是家训,亦象征岭南文化经世致用、海纳百川之气候。而其交游亦不拘一格,任侠豪迈。中国菜系分呈,而因“天下所有食货,粤地几尽有之”,粤菜亦天然具有触类而旁通的基因。北上与鲁菜交融,而成官府菜的谭家菜为一例;自成一统流转于喷鼻香江的太史菜亦为一端。这是中国人“调和鼎鼐”的功夫。至喷鼻香港,原是中西交汇之地,涌现了所谓“fusion”(领悟)菜系。《燕食记》的荣师傅与五举,在传与变中载浮载沉。而五举因入赘海上厨家,更将粤菜与本帮菜交融,发明“水晶生煎”“黄鱼烧卖”“叉烧蟹壳黄”,这是温和的改良。而具冲击的,则是其徒露露,将椰奶用来为“青鱼汤卷”发色,露露道:“我们马来的叻沙汤头,放得椰奶;泰国的冬阴功,也放得椰奶。怎么就你们上海菜放不得?”这是关于饮食的寻衅,亦是时期之音。何谓正统、何谓规矩并无定论。发嬗,变革,原便是这么一言而振聋发聩。
《北鸢》中克俞在西泠印社附近开了家菜馆,叫“苏舍”。菜单开头写着苏子瞻的句:“未成小隐聊中隐,可得长闲胜暂闲。”可谓人生自喻。隐,其大约天然与饮食攸关。宋元时饮食大盛,其含对士人的爱崇。从苏轼、黄庭坚到陆游,留下不少评论辩论饮食的诗文,如《西湖老人繁盛录》《梦粱录》《武林往事》等。至今日,以用舍行藏之“隐”意对待时期常变之心,依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端。《燕食记》中写了几位“隐士”,也是厨师。首先是慧生的“隐蔽”,是为了母子二人于浊世的安然,万千本领不可显山露水,一道“璧藏珍”内有天机;其二是叶七的“隐逸”,作为昔日的洪门魁首,反清落幕隐于民间,如渐凉的陈皮红豆沙封印手艺;其三是五举的“哑忍”,在时期迭转和个人命运的落潮中,将“十八行”退守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区。他们或是韬光,或是养晦,于韶光有如珠蚌之约。
更可推演的因此隐而变,乃至两者的辩证。《燕食记》中年轻的荣师傅创造了造诣莲蓉月饼的窍门,在于放盐。庖界行尊韩世江总结道:“盐是百味之宗,又能调百味之鲜。莲蓉是甜的,我们便总想着,要将这甜,再往高处托上几分。却时常忘了万物有序,相左者亦能相生。好比是人,再锦上添花,不算是真的好。经由了对手,将你挡一挡,斗一斗,倒斗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来。盐便是这个对手,斗完了你,玉成了你的好,将这好味道吊出来。它便藏了起来,隐而不见。”其如微末,又居功至伟,推波助澜,可造就历史大势。由此可见的,是有关时期的行藏之术。在小说中,笔者重点写到了叫“音姑姑”的人。1940年代,岭南抗日之声愈炽,便有人借之为号令,游刃集结民间各种力量。抗敌,则胶结凝聚,如万千蚍蜉共撼树;得胜,则如蚁而散,各归其巢。不囿于团体、政见,只以任务为要。个中的枢纽人士,被称为“音线”。其音希声,难觅踪迹。由此可见,共成抗战伟业的大条件下,广东民间海纳百川,聚散有序,如“东江纵队”的发嬗与造诣可视为范例。而音姑姑等“音线”如盐的隐现,恰成为以微而知著的关键。
大象无形,味的辩证形同此理。最美的勾勒,一如李凤公教画,白宣一张,倏忽可见雪地银驹。饮食可见隐现之道,虽稍纵即逝,却如一瞥惊鸿。韩世忠师傅在月饼中的隐蔽,是家国情怀的深奥深厚。当被公布于世的那一瞬,宏宏于天日,造就的是个人的高义,更是历史的高光。(葛亮)
来源:新华逐日电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