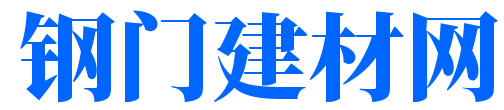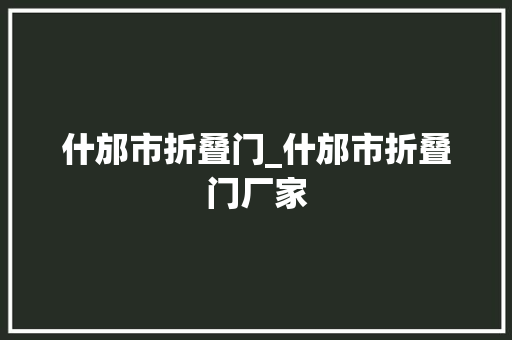散文||西曲沟系列故事|南磨
作者:老姜
0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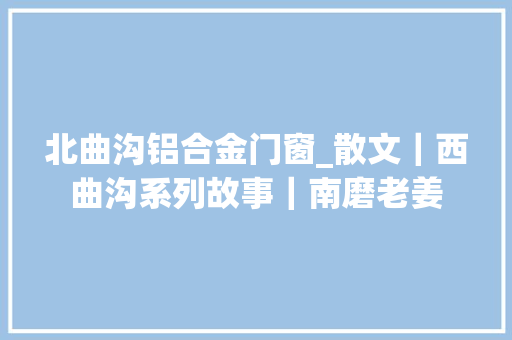
这个题目已经让我纠结了良久,以是至今码起字来心里还是以为有点忐忑。
写本村落题材的作品是很让工资难的:写的好了,说你胡吹,写的不好了,说你水平有限。实事求是吧,年轻人说你胡诌,轻微艺术点吧,过来人又说你是凭空杜撰。
比如说,写西曲沟的南磨吧,恐怕就得先从南河提及。由于南磨只是南河河道上的一个节点,没有南河哪来的南磨?这说着说着话不就长了?
实在南河只是仅限于西曲沟的一种叫法。同是高平方向来的一条河,就由于流过村落落的方位不同,其称谓才有了差别。西曲沟之以是叫“南河”,那是由于这条河从西曲沟村落庄的南面流过,而曲沟集的人称作“北大河”则是由于河在曲沟集的北边。南河也好,北河也罢,实在说的都是同一条河,那便是万金渠。
万金渠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。点点滴滴、涓涓潺潺、浩浩荡荡、曲曲弯弯,让人感慨,让人惊叹,让人回味、让人眷恋,有时让人热泪盈眶,有时也会让人浮想联翩......
万金渠的历史很悠久。据《安阳县志》记载,始建于唐朝。唐咸亨三年(公元672年),相州刺史李景自西高平村落筑堰,引洹水入渠东流溉田,注入广润坡,当时取名为高平渠。北宋至和年间,韩琦疏通高平渠,自相州城西引渠水沿城北流,分水入城,安装水磨,建湖修亭,供人游览,同时把高平渠改名为千金渠。到了元代,千金渠淤积,再次开导、清淤,因“以渠岁所灌溉,利不下万金”,遂改名万金渠,并且一贯沿用至今。
万金渠上闸口不多。但据我理解,至少有两道闸口是很有名的。首先是西曲沟西地耶,西南洼的那个闸口,便是永定村落西北的那个。这个闸口的水面落差比较大,大约有七八米高。它的浸染有两个:一是通过闸口抬高水位,让一部分河水流向二支渠,并通过二支渠一贯向北,去灌溉陈家井、直至超越铁路流到西夏寒等村落,其利民代价难以估算。其二便是通过两个口径大约三十来公分的水轮泵,把水位上扬四五米,通过一条断面不到一个平方的小渠儿向北流淌。在向北大约二百来米的地方有个丁字渠口,向西,可以灌溉西曲沟村落西南洼的地块,向东,则可经由西曲沟的林园、科研组、张家桥,到西曲沟村落西头,然后向北,通过三个翻水洞、超越通往前后街的两条大路和后地耶那条老马路,再沿着老马路北边一贯向东,流往北曲沟。由于这条小渠儿在流向北曲沟的途中把大块地“分割”成了南北两段,村落民为了能精准的指明地块的方位,“小渠儿北”这个地标性的地名便应运而生了。
二支渠不才,小渠儿在上,因两条渠水路方向不同,渠道之间便有了夹角。由于耕种不便,韶光久了便硬生生的造就了一处芦苇荡。
微风吹来,芦苇婆娑,摇扭捏晃,像娉娉袅袅的豆蔻少女练功一样摇荡着身姿,无序的变换,其实令民气旷神怡。清清的万金渠水通过西南洼的闸口,跌落出朵朵水花儿,在短暂的亮相之后又和它的伙伴一起顺着河床一起向北,又转而向东。小弯曲、大弯曲,充满在路途之上,年夜进、迂回、缓急、起伏,之后,它们依然初心不改,仍旧争先恐后的一起向前!
它们超越张家桥,漫过南坑,纷纭到西曲沟南磨闸口前集结待命。它们就像一彪刚刚打了一场恶仗的军队,在这里作短暂的盘旋和休整,彷佛是在等待命令。它们把水磨硕大的水轮盘看作是一座城堡,随时准备向其发起猛攻!
02
南河岸上的耕地是西曲沟村落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所在,无论春耕夏种还是秋收冬藏,都须要超越一座桥。这座桥便是至今仍旧在用的石桥,当时取名叫“漫水桥”。
为什么叫漫水桥呢?提及来这里面还有一段让民气酸的往事....
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当时南河北岸上向东有一条路,顺道走大约百十来米,再往南上个小坡就上了这座桥,过了这座桥就到了河南岸的东南路上。往东可去曲沟集,往南则通往永定、鄣邓。这座桥很高,但只有中间一个桥拱,其它部分全是实芯。咋一看,区区万金渠水流经这么一座“高大上”的桥,彷佛以为有点不成比例。可便是这座桥,却给西曲沟带来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大灾害。
一九六三年的农历六月间,阴雨连绵。老天拿着劲儿整整下了七天七夜还不敷兴,弄得上游水库水位暴涨,村落庄更是泽国一片。为了水库安全,政府有关部门决定于农历六月十九开始泄洪。这天下午两三点,滚滚大水立头齐岸,犹如山呼海啸一样平常,它们猖獗地卷着骡马牛羊,肆意般裹着木石梁檩,飘着滚瓜肚圆的西瓜甜瓜、整颗整颗的大树、整垛整垛的麦稷,乃至还有来不及下葬的棺材,在阵阵刺耳的哀鸣和嚎啕声中顺着万金渠一起向东狂奔......
这时,横亘在南河上、平日里从不把万金渠水放在眼里的这座桥顿时傻了眼:长粗短落的东西来不及“吞咽”,纷纭被挡在了表面。水越挡越大,乱七八糟的东西便越来越多,东西越多便挡得越来越严,挡得越严水位便越来越高,终于不才午三四点钟给西曲沟酿成了一次特大的洪涝磨难,而且是有史空前。大街成了河床,水深湍急,不知冲毁冲塌了多少房屋,尤其是住在南河岸上的人家险些没有一家能够幸免。当时也曾有人建议用炸药把桥炸掉,怎奈,考虑到连续下了七天七夜,村落民的屋子早已被水泡了个透透,万逐一声巨响,震塌了村落民的房屋又该咋办?经权衡再三,末了只好作罢。
洪灾过后,政府出资要在南磨闸口上边重新建筑一座新桥。为了接管教训,就把这座桥设计成了“漫水桥”的样子。建造时,在桥高下的北河边上,专门铺设了几十米整块整块的子母石,仅露出水面尺把高,那是专门为妇女们洗衣裳而设计的。以是,无论白天还是傍黑儿,只要天不下雨,便会看到排得整整洁齐的大姑娘小媳妇,坐在河边,净水摆、双手搓、棒槌打、俩人拧,欢声笑语、好不惬意!
那情景不仅惹得过路人眼馋,还让周边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倾慕妒忌恨,默默发出“嫁人就嫁西曲沟”的誓言!
03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到西曲沟南磨上磨面的都是三里五村落的乡民。久而久之,“南磨”便成了一个地标性的称谓,竟然和“前街东头儿”、“胡同口儿”、“互助社门廊儿”、“南河头上”等称呼一样齐名了。
实在,到南磨上磨面是蛮讲究的。首先要“淘麦的”。“淘麦的”须要用个柳条簸箩,一个水缸半缸水,一个竹篮子。“淘麦的”时往竹篮里放三分之一的小麦,沉到水缸里,一手提篮,一手搅拌,然后拎起来空水,等篮子底下不流水了,就可以倒到簸箩里了。当然,中间水脏了是要及时换掉的。
其次是抹麦子。抹麦子是用拧干了水的毛巾将簸箩里的麦子抹擦一遍,就像擦身子一样的来回抹。抹一次要去水里摆一次毛巾,直到毛巾干净了为止。
再次便是捡碜。一样平常是两个人对面,分别坐到簸箩的两边,一把一把的分拣。如果人手多的话,就可以用簸箕装布袋了。装布袋的时候也是有说处的,这便是要先旁边晃几下,土话叫“虽”(音sui), 这样可以让麦粒在前,麦碜、杂质在后,如此反复,便会把麦子弄得干干净净。
末了便是醒,俗话叫“支应(音)”,像醒面一样,让麦子里外都能分享到所沾有的水分。这个过程是通过送到磨上,过了秤、交了钱,在排队期待中自然完成的。
磨房在南河头上北岸路南的。这是一座建在河上的建筑,下面便是水磨的水轮。磨房的东西两个方向都留有两个小窗户。通过东边的窗户可以看到滚滚东去的万金渠水和蜿蜒的两岸,其景致美不胜收。透过西面的窗口,可以瞥见水面如镜的河水,它们在那里缓缓地盘旋,就像一群等待命令军人。
磨坊的主角是那盘石磨。这盘石磨的直径大约六尺旁边,厚度少说也有尺半。和一样平常石磨最大的差异是,一样平常的石磨是上扇转,而面前的这盘石磨却是下扇转。只见上扇的磨盘上对称的插着两根半尺粗的木杠,分别用绳子拴在墙上的“拴马石”上。下扇被磨坊下面伸上来的一根硕大的木柱顶着,离地面大约二尺多高。下扇的底部有尺把宽的铁皮托盘,外沿还向上折有三四寸高的边。靠近西边的窗口,离窗口大约三尺有余有一根柱子,上面有条绳子一贯延伸到窗外,连接着掌握水磨的水闸开关。
轮到我们家上磨了,我和母亲一起走进了磨坊。我们把要磨的小麦倒在地上,用簸箕把麦子送到磨盘上,母亲见告我说,这叫添磨。
统统准备就绪,管水磨的人便撸起袖子逐步的拉起绳索。绳索连着掌握水磨的水闸开关,水闸紧连着一个三四尺宽的“水簸箕”。为了担保水力能够集中,“水簸箕”上宽下窄,为了让水力保持冲劲儿,“水簸箕”与地面形成约三十度旁边的夹角,并直接把水引向水磨的水轮盘。
随着水闸门的逐步开启,那些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河水,争先恐后的跑进“水簸箕”,并集中力量顺坡猛冲。只见它们碰在硕大的水轮上,溅起尺把高的水花,那水轮却纹丝不动。然而,它们前赴后继、不离不弃。随着闸门越开越大,水流越来越多,冲力越来越猛,那水轮终于逐步被打转了......
随着那石磨“格叽格叽”的迁徙改变,磨缝里便垂垂流出了“森森乐乐(音)”的麦瓣,这便是麸皮。托盘里的麸皮逐渐多了起来,管磨的人从边上拿起一个很不规则的东西,瞬间套到托盘上,并顺手挂到一个柱子上,只见托盘固定在那个地方,把托盘里的麸皮儿刮到了地上。
母亲扫了一片地方,拿起一个三四尺长,两头像板凳腿样子容貌的东西,能四个脚平稳的趴在地上。中间有两根两寸宽且非常光滑的方木橧相连,两根相隔六七寸宽。母亲说,这是箩床子,是专门供箩面用的。母亲拿起一个萝面的萝,盛上麸皮,放到箩床上,前后一拉,瞬间,那洁白的面粉便逐步的落了下来......
母亲说,要搁别的地方,有法儿的人家儿(有钱有势)都是驴拉磨,没法儿的人家儿(穷苦人家)都是几家合资轮班推磨。西曲沟人有福泽,家家用的都是龙扯磨。
“龙扯磨?”我有点儿好奇。母亲见告我,龙王在水晶宫,水都归他管,因此,用水打的磨就叫“龙扯磨”,磨坊供的也都是龙王的牌位。
现在想来,别说耕种秋收,就单单是得手的粮食要弄到嘴里,还得要经由淘麦子、抹麦子、捡碜、支应,添磨、箩面,再生的做成熟的,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怪不得古人要给子孙留下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”的家训,这确实是来处不易呀!
04
上世纪九十年代,万金渠的水流量越来越少,随之被向南改道,成了地下渠。从此,南河、南磨便成了西曲沟人的影象。就在截稿的前几天,我专程来到南河。只见通往原来老南桥的路仍旧清晰可见,只是那几间老磨坊,已经仅仅剩下贱丝般的哽咽。虽然还是原来的旧样子容貌,却早已被光阴剥离的体无完肤,不由得让民气酸、落泪。
我站在漫水桥上,把目光投向桥的北面,想再看看当年的洗衣石,是否还在桥的两边,能否回味一下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笑声串串。可惜,可惜它们早已经被垃圾掩埋,我什么也没有瞥见!
我站在漫水桥上,想看看龙扯磨的那两处拱圈,可它们已经险些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,只剩下像眉毛一样弯弯的上弦!
我站在漫水桥上,向东望去,昔日的河床虽是依稀可见,可怎么也找不到昔日的容颜。
我站在漫水桥上,向西远眺,企图想象一下南河之水天上来的壮不雅观,怎奈,我两眼模糊,顿时便什么也看不见!
我想走,我想回去,可自己的两条腿不怎么听我使唤。我静下心,做了一下深呼吸,微微的闭上我的双眼。逐步的,逐步的,彷佛从南边那盘水碾的方向飘来了“丝丝”的声响,彷佛它在“吱吱”的叫喊。仔细聆听,彷佛中间那三组水轮机组也在“嗯哼哼哼”的感叹。弹花柜那高低变革的“翁翁”声,彷佛在演奏自己的和弦,那盘水磨仿佛在“吱扭吱扭、嗯哈嗯哈”的低吟浅唱,只是听得有点悲惨!
唯有空中偶尔飘来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铜铃般的笑声,一串,一串,近了,却又渐远......
几十年未曾听到的协奏曲呀,本日仿佛又响在了我的耳边......
我瞬间猛醒:弗成,我不能连续保持沉默!
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纠结。我以为我该当拿起笔,见告我们西曲沟的村落民、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,南河、南磨,曾经是我们西曲沟父老乡亲、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!
二〇一九年一月六日于西曲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