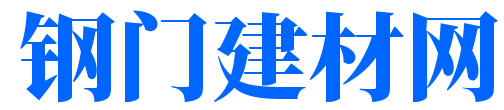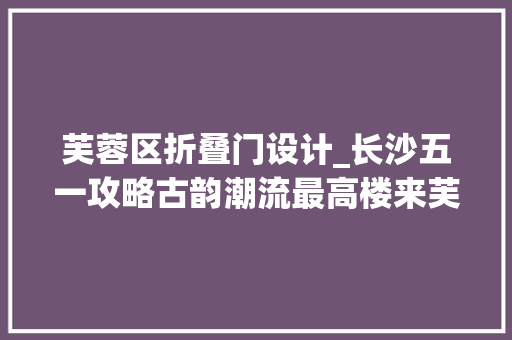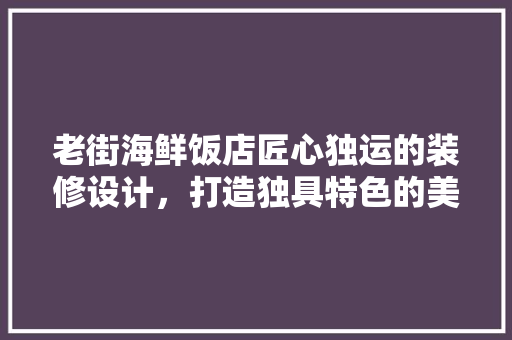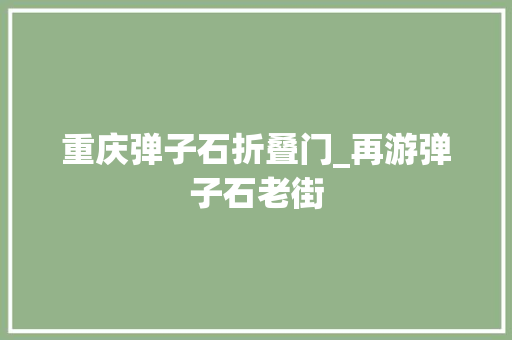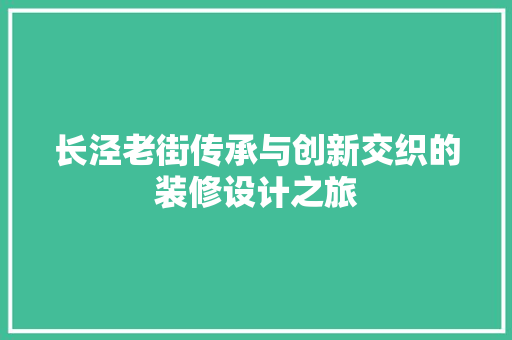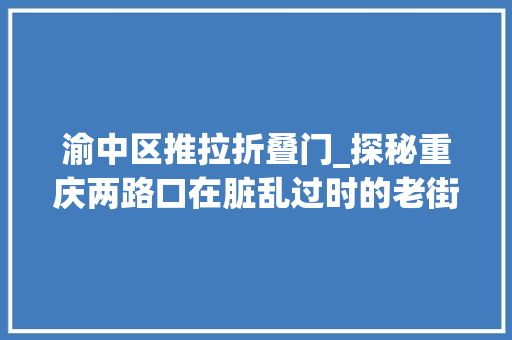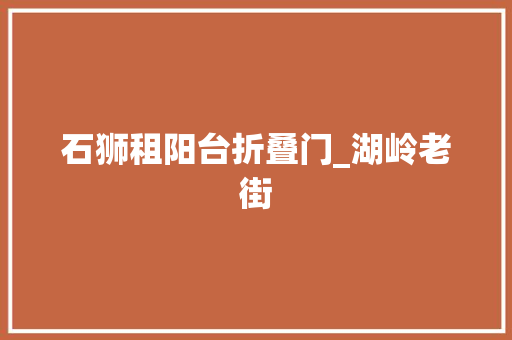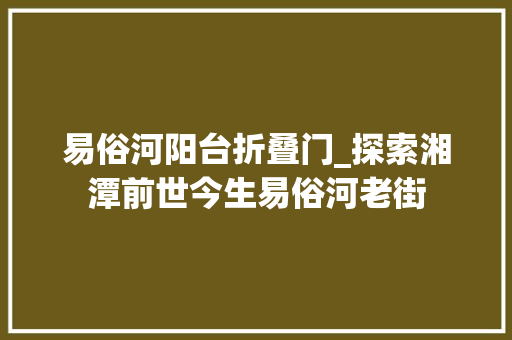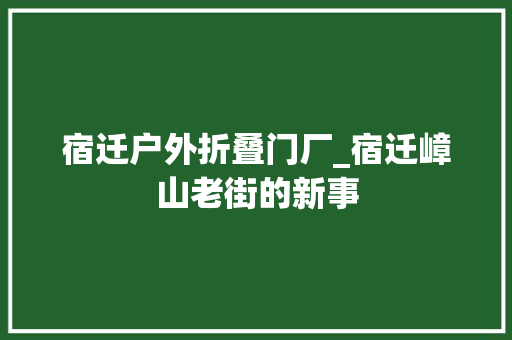全文约3300字,阅读须要15分钟
从无锡到杨桥老街,自驾用不了一小时车程。从锡宜高速的和桥出口下来,按行车导航提示,经省道拐进一条乡道,两边涌现了成片的庄稼地,行道树已经成荫,几百米之后就到了杨桥老街的入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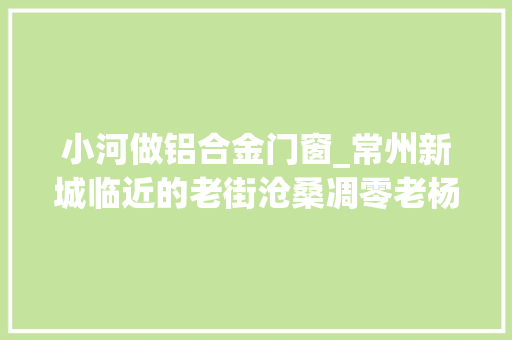
杨桥老街入口
这是一个新修的仿旧门楼,土气而粗陋,两边是新修的围墙,路侧有一个很大的杨桥老街的导游舆图,一两棵老树歪歪斜斜地立在一旁,扭曲的树枝向舆图伸展着。一条老狗
杨桥老街地处常州市武进区,与无锡市宜兴的和桥古镇相邻,之间不过三五里路。近年在网络媒体上涌现频率颇高,是一个在兴建特色小镇热潮中推出的老镇老村落修复项目,也是常州留下来的并不多见的江南古镇——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,江苏目前所遗存的江南古镇,以苏州居多,无锡次之,常州最少。我曾经想过,这种苏锡常从东往西逐渐减少的古镇遗迹,究竟是由于几十年间的破旧立新所致,还是原来便是这种状况?
筐里的老油条和晾着的咸菜
杨桥老街门楼朝南,连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灰缝,觉得不是江南村落庄粉墙黛瓦的风格,却似徽派古村落老街建筑的样子容貌。走进门楼是一条不宽的直街,两边的屋子该当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,当时进入了改革开放,江南州里企业风起云涌,屯子富得很快,人们拆旧建新,大体都是这种两层楼房,后来逐年改造装修,换上了铝合金门窗和防盗门——从前的屯子小镇旧巷是常常户不闭门的,哪里用得着什么防盗门。几十米长的街边,只有一两家小店铺,一家卖些日杂,一家卖些小吃,大约是清晨卖剩下的几根油条,偃头搭脑地歪在篓筐里,窗边的一根绳子上挂着一些干瘪的咸菜。
小街上几无人影,唯有几只在屋角打盹的老母鸡和东张西望的猫狗。忽然听得几声狗叫,有两个女人从那头走来,一老一少,偶尔摆个姿势,用手机拍张照片,听口音是北方来的。冒昧问了一句,她们说是看了网上先容慕名而来,进去转了一圈,很是失落望。
这种小街江南老镇常见
小街北端大约十几米明显变得狭隘起来,两边的屋子年代也久远很多,是那种半边木门半边木窗的格局,一看就知道是旧时屯子老街经商的临街铺子。斑驳的老墙上挂着“常州市一样平常不可移动文物”的牌子,虽然没有注明建造的年代,但表明是有些保存代价的了。这些屋子都是大门紧锁,透过窗缝门缝看看,里面大致都是破败零落,散发着霉尘味儿,那味儿细碎而隐约,却挥之难去。
这一段老街的顶头是一座古桥,江南最常见的单孔花岗岩全拱石桥,石头桥身,石头桥栏,石板桥面,年永日久,全长十多米,桥宽二米多,石桥整体无缺,但已经略有变形,桥面石阶亦有歪斜,桥身侧面照例长着一些草木,细细斜斜的,没有常日会见到的石榴树。这便是杨桥老街最为宝贵的建筑“南杨桥”,桥是贯通杨桥南北的必经通道,也是过去武进县与宜兴县的分界。听说此桥初建于明初,原来是用老杨树建造,杨桥之名即此而来。清代康熙与道光年间曾几次重修,改成了花岗岩石桥。2008年,南杨桥被公布为常州市文保单位。
市级文保单位南杨桥
南杨桥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运河,桥南沿河向东,并无遗迹可不雅观。沿河向西,有原来的老码头,救火会,药店,茶楼,米行,糟坊,新四军秘密交通站等旧迹,平房与二层楼房间杂。走过去不及百米,已到尽头。码头不大,并非那种水陆交通的大格局,只比平凡江南邻水人家的私家码头略大而已。新四军的交通站,据先容属于当时的太湖游击队,明面上是一家铁匠铺,隔壁一位老者见告我,后来良久这里一贯是当铁匠铺的。可惜如今装了个蓝色的铁皮大门,令人看了不知所云。
走过南杨桥,就进入到杨桥老街的主体部分。看得出这部分建筑大体是从前留下来的,最近经由了修缮,但修缮的质量并不太好,那些重修的山墙、门面、风火墙,都是青砖灰缝,靠近于徽派风格,木门一律油漆成靠近玄色,与旧时的江熏风貌相距略有点远。我私下惊叹能把这些老建筑都保留到现在,却并不赞许修复的风格,心里琢磨:这主持建筑的团队是怎么想的?是为了节省用度呢,还是为了在江南古镇老街修复中独树一帜?
新四军交通站旧址
杨桥老街的主体部分有两条街,一条南北走向,一条东西走向,形成一个十字。东西走向的街不长,两头不过百来米便是从南杨桥下运河分出的由南向北的小河,一东一西把老街围裹在内,东西两条河上都有桥向外沟通,但桥另一端已是老街之外了。
老街的石板路已经破旧,高低不平的路面,青苔斑驳,杂草零散,逐步地踩着这样老路,走着,走着,就抱负起了那从前的光阴,那时的老街,那时的行人……朴实的农夫到街上来抓一副中药,或者买点日杂用品;刁滑的贩子在想着怎么赚一点别人的便宜,能不能把别人刚才送进当铺那个玉镯低价赎出来;那位铁匠师傅一边打铁一边谋划着傍晚时乘着暮霭去送那份情报;住在大院里的朱姓乡长是这个小镇的最高主座,正在期待宴请县里来的官员;临街楼上有绣女正在飞针走线,为乡长太太绣花的这件旗袍,可以换来几天的花销;离码头不远的糟坊又出了一缸新酒,酒喷鼻香撩人,吸引了街上险些全体男人……
这么想着,我走完了老街的边边角角。杨桥老街真的好小哦!
这时我终于明白为何杨桥乡政府后来要放弃这块地方,择地另建新街和办公之所,由于这老街地盘的狭隘逼仄,完备不适宜做一处公民公社的经济文化中央。也由于这样,这处老街没有被拆建改造,得以较好地保存了原来的风貌。
牧斋园
院内早已破败不堪
杨桥老街里并没有出过什么名人,最显赫的一座宅院是“牧斋院”,牧斋师长西席是晚清秀才,他的一位后代学医,出任过杨桥乡长和武进中医院院长。“牧斋院”在北街,早已破败不堪,居然这次丝毫没有被修复,从倒塌的院墙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内的荒凉颓圮。其余有一座洪家大院,还有一座堵家大院,堵家本是安徽贩子,行商赢利之后就在杨桥街上买地建园造房,定居下来。洪家和堵家两座宅院是建筑了的,但都是大门紧闭不纳游客。
杨桥老街给我最大觉得是人气稀冷。走了一圈,没有看到什么人,更别说人来人往了。只有几个老人孤独地坐在旧屋门前,无精打采的闲坐,乃至你走过,那偶尔看一眼也是毫无激情亲切。那是一个仲春的下午,天有点阴,这杨桥老街彷佛也是呼应着静默而无趣,犹如一个走到了末端的生命,清清凄凄且阴阴冷冷的。
在一座老宅前遇见一位老人。老人说:这条横街到了晚上,就他一个人住着,特殊的安静。年轻人都早已搬出去住新楼了,许多老人也搬走了。本来还有一些打工的外地人租住,可是有人出钱修复老街,开拓旅游,把租住的人都弄走了。结果旅游没开拓成,根本没有什么有人过来,老街就冷落如此了。
关帝庙
南杨桥东侧有一座关帝庙,庙旁有一个如戏台般的建筑,挂了一块牌子“南杨宴”。进来时大门紧闭,走完老街离开时却瞥见大门洞开。探头去看,一位大妈激情亲切呼唤。交谈之下,得知这处房产本属供销社,大妈盘下来开了这家饭店,招牌便是“南杨宴”。虽然游客不多,但预约上门用饭的客人还好,以附近周边客人居多,也有上海等地老年人组团来玩,顺便就地吃点什么风味特色。由于是杨桥老街唯一的饭店,买卖还能支撑。大妈说:往后携同伙来玩,可以预约订餐哦!
离开杨桥老街时,我在“南杨桥”的石栏上坐了一会。访游古镇老街,照例该当找一家茶馆坐坐,但这儿却没有茶馆。桥下的河水了无波澜,没有航船经由,估计这河流的通航功能基本没有了。江南古镇老街险些都是地处水路交通要津,没了通航就即是没有了脉动,昔日热闹的老街,如今人少气冷,亦是一定。至于建筑开拓失落败,那便是一个比较繁芜的问题了。
老树还是蛮上镜的
历史犹如桥下流水,流淌不息,一程一程,永久不会在某一程勾留。置身于某个时段的人们却不肯循分,不愿仅仅知足于面前的生存和体验,总是企求“诗与远方”。“诗与远方”朝着两个方向:以往和未来,思念以往生活的体验,追求未来生活的空想。古镇老街就用“以往生活”供应人们思念并体验的场景。江南第一个古镇周庄开拓之后的轰动,台湾作家三毛进入周庄之后的热泪抒怀,都是他们亲历那些以往生活的色彩、调性、民俗、风情、故事、氛围、关系、节奏,从中得到了体验,感悟,由于亲近而被“诗与远方”触动心灵。而杨桥老街,能给人什么以往的思念和体验呢?显然是零星、贫乏且缺失落亲近的,失落败也就不足为奇。
前几天才看过一份特色小镇“去世亡名单”,险些所有遭遇失落败的特色小镇都有相似的问题:如果古镇老街不能供应令人亲近的以往生活体验场景,如果新型小镇不能供应令人惊喜的未来生活体验场景,就不能知足人们对“诗与远方”的碎碎念念,一定难以成功!
老街顶头坐着的两位寂寞老人
驾车拜别。驶向新的目的地,与沧桑凋零的老杨桥越离越远。听见那条年轻的狗又在叫,响亮,却不亲近。